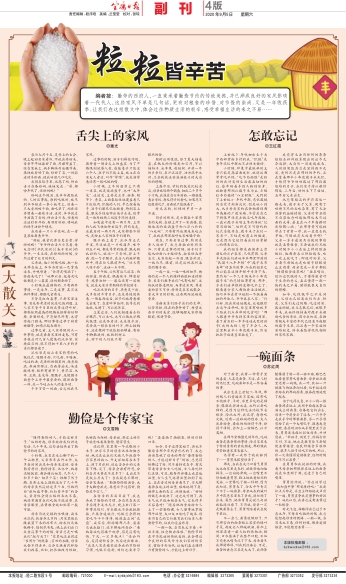本期发布:
怎敢忘记
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于关中西部贫瘠乡村的我,“饥饿”是童年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关键词。
小时候,印象中最依赖的主食只能是高粱面发糕,就连这都常常吃不饱。“吃个白面馍”是幼时的我对美好生活最真切的向往。每年掰着手指头盼到除夕,就盼着那碗以糜子米为主、点缀红枣白糖的“八宝甜饭”。大约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忍饥挨饿的感觉才渐渐淡化。但是从小到大,从乡村老家的农舍栖居到都市高层的广厦安居,不管是自己下厨张罗还是去饭店吃年夜饭,一盘以糜子米唱主角的传统“忆苦思甜饭”,始终是不可替代的仪式感般存在。糜子米于我们一家老少,不仅是味蕾上的偏爱,更是因为它延续着我们刻骨铭心的绵长记忆。
我的祖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户农家,几代贫困。父亲多次给我们讲从爷爷那里听到的“民国十八年年馑”中“糜子米吊长命”的真实故事,而我的祖辈之所以能在这场年馑中幸存下来,竟然与“一个儿子换来半小布兜糜子米”的悲情故事有关。那年,乡亲们连草根树皮都吃不上了,眼看着全家人都快要活活饿死,恰巧爷爷在村口碰到一个挑着扁担的外地人。爷爷哀求人家:“行行好,把我家娃娃抱走,让他跟你去逃个活命吧。你筐里有啥就多少给我们点吊命的吃食吧!”那人跟着爷爷来到家里的窑洞里,看了看当时一岁多哇哇大哭的孩子(我的大伯),想了半会儿,从筐里取出半小布兜糜子米,然后把孩子放进筐里挑走了。
我觉得无法用任何的条条框框去评判祖辈做出的这个无奈选择。大自然一旦发起威来,人的招架能力总是显得微不足道,更何况是在那样的年代。正是靠着那半小布兜糜子米充饥,才使得爷爷奶奶挨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,我们家才得以赓续绵延。三年后,奶奶生下了姑姑,五年后父亲出生。
从悲催暗淡的岁月深处一路走来,糜子米于父辈,便有了咀嚼不尽的五味杂陈,有了无法割舍的血脉情愫。父亲时常会情不自禁地念叨起他那从未见过面的大哥,甚至在八十岁高龄时还难解心病:“我那哥哥可能被带去了甘肃一带,我一直想去找寻他,可惜就是无处着手啊!”父亲一辈子最深恶痛绝的事情就是浪费粮食,不要说我们兄妹小时候不小心在地上掉的馍渣饭粒,他都要求必须捡起来,吹一吹土就吃了;即使对孙辈,父亲看见剩饭也是吹胡子瞪眼制止没商量。母亲更是一辈子都把“糟蹋粮食造罪呢!”挂在嘴边。经历过饥饿的人,才懂得粮食对于生存的意义,真正懂得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,懂得敬畏大自然的馈赠。
如今,吃饱饭早已不是问题,父母也已经离我们而去。但是,父辈们走过的路、吃过的苦、挨过的饿,我又怎敢忘记。就像多年来,我始终保持着对糜子米超越吃食的亲近。因为我知道,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已经毫不起眼的糜子米里,沉淀着一个家族的苦难秘史,传承着值得代代相传的家风家教。
小时候,印象中最依赖的主食只能是高粱面发糕,就连这都常常吃不饱。“吃个白面馍”是幼时的我对美好生活最真切的向往。每年掰着手指头盼到除夕,就盼着那碗以糜子米为主、点缀红枣白糖的“八宝甜饭”。大约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忍饥挨饿的感觉才渐渐淡化。但是从小到大,从乡村老家的农舍栖居到都市高层的广厦安居,不管是自己下厨张罗还是去饭店吃年夜饭,一盘以糜子米唱主角的传统“忆苦思甜饭”,始终是不可替代的仪式感般存在。糜子米于我们一家老少,不仅是味蕾上的偏爱,更是因为它延续着我们刻骨铭心的绵长记忆。
我的祖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户农家,几代贫困。父亲多次给我们讲从爷爷那里听到的“民国十八年年馑”中“糜子米吊长命”的真实故事,而我的祖辈之所以能在这场年馑中幸存下来,竟然与“一个儿子换来半小布兜糜子米”的悲情故事有关。那年,乡亲们连草根树皮都吃不上了,眼看着全家人都快要活活饿死,恰巧爷爷在村口碰到一个挑着扁担的外地人。爷爷哀求人家:“行行好,把我家娃娃抱走,让他跟你去逃个活命吧。你筐里有啥就多少给我们点吊命的吃食吧!”那人跟着爷爷来到家里的窑洞里,看了看当时一岁多哇哇大哭的孩子(我的大伯),想了半会儿,从筐里取出半小布兜糜子米,然后把孩子放进筐里挑走了。
我觉得无法用任何的条条框框去评判祖辈做出的这个无奈选择。大自然一旦发起威来,人的招架能力总是显得微不足道,更何况是在那样的年代。正是靠着那半小布兜糜子米充饥,才使得爷爷奶奶挨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,我们家才得以赓续绵延。三年后,奶奶生下了姑姑,五年后父亲出生。
从悲催暗淡的岁月深处一路走来,糜子米于父辈,便有了咀嚼不尽的五味杂陈,有了无法割舍的血脉情愫。父亲时常会情不自禁地念叨起他那从未见过面的大哥,甚至在八十岁高龄时还难解心病:“我那哥哥可能被带去了甘肃一带,我一直想去找寻他,可惜就是无处着手啊!”父亲一辈子最深恶痛绝的事情就是浪费粮食,不要说我们兄妹小时候不小心在地上掉的馍渣饭粒,他都要求必须捡起来,吹一吹土就吃了;即使对孙辈,父亲看见剩饭也是吹胡子瞪眼制止没商量。母亲更是一辈子都把“糟蹋粮食造罪呢!”挂在嘴边。经历过饥饿的人,才懂得粮食对于生存的意义,真正懂得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,懂得敬畏大自然的馈赠。
如今,吃饱饭早已不是问题,父母也已经离我们而去。但是,父辈们走过的路、吃过的苦、挨过的饿,我又怎敢忘记。就像多年来,我始终保持着对糜子米超越吃食的亲近。因为我知道,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已经毫不起眼的糜子米里,沉淀着一个家族的苦难秘史,传承着值得代代相传的家风家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