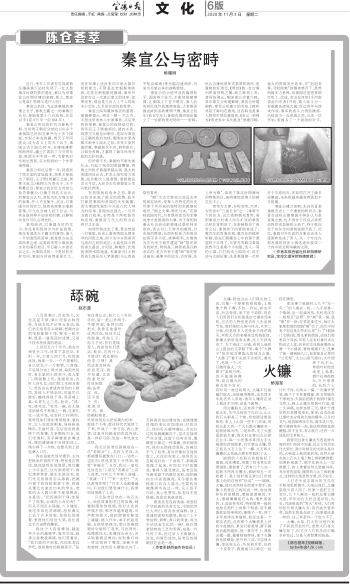本期发布:
舔碗
八百里秦川,历史悠久,文化沉淀丰厚。秦川西部古称西府,当地农民不论男女老幼,他们吃完饭用舌头舔碗,把碗内沾的米粒都舔干净,要求一粒不剩,既是一道亮丽的风景,又是个技术性很高的绝活。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在市级机关工作,经常下县驻队,多则一年,少者三四个月。吃的是派饭,每家一天,一户户挨着轮。自己给农户一斤粮票、三角钱,不足部分由上级补助。每到吃饭时,有主家的小孩来叫。进入家门,便脱鞋上炕,盘腿而坐。农村人讲礼仪,他们把工作组当客人,吃饭由长者或有身份的人陪同,其他人不能坐炕。炕桌早已摆好,擦抹得很干净,饭菜端上桌,长者礼让三先,他说:“请,吃,请吃饭。”吃完一碗,由儿媳或姑娘双手再端上一碗,这套礼仪一成不变。在农村工作期间,我发现他们特别爱惜粮食。夏收时,大人在前面割麦,娃娃排成横队,手提竹篮,在后面觅拾遗掉下的麦穗,力争颗粒归仓。他们吃馍时,双手捧着就在嘴边吃,馍的渣渣就不会掉到地上,偶尔掉下一半粒,也要从地上拾起塞入口内。
我在每家吃饭时看到,主妇把锅底铲得很干净,特别是打搅团,锅底留的饭底很厚,她们撒上少许盐巴,灶内添柴焙干,锅巴烤得焦黄,脆生生很好吃。他们吃完饭都用舌头舔碗,把碗内留下的饭粒都舔干净。我是从豫北农家走出来的学生,老家的大人教训孩子爱惜粮食,总是说:“把饭碗刮干净,如留下了饭根,会减你小命的寿!”但从不用舌头舔碗。入乡随俗,我吃毕饭也学舔碗,脸和鼻尖上沾了许多饭粒,花脸似的难看,惹得他们哈哈大笑,急忙递过毛巾或帮我擦拭。
我这个人有股犟劲,越是学不会的越要学。每吃毕饭,就请主家教我舔碗,他们笑着说,“我们舔的不到家,你向张老汉学吧,他是俺村的舔碗高手。”张老汉我认识,他六七十岁的年纪,留一把山羊胡子,手脚利索,是种田的把式。我曾在他家吃过两次饭,但没见过他舔碗。问他儿子,他儿子说,你们是城里人,我爸怕你们笑话。我说,这有什么可笑话?我还要向他学习哩!我的话是否转告给张老汉,我不知道。又在他家吃饭时说到舔碗,张老汉说,还不是个穷,老祖宗节约,爱惜颗粒粮食,吃罢饭用舌头把饭碗内的米粒舔个干净,就这样代代延续了下来,形成了一种习俗。我心里想,这是节约粮食的优良传统,是一种好习俗,也是一种饮食文化吧。
我见识张老汉舔碗是在一次“老碗会”上。农村人吃饭,大都端着饭碗聚在门口,一边吃一边扯闲,说说笑笑十分热闹,故称“老碗会”。当时,我从一家吃过饭走出门,就见“老碗会”上有人起哄,只听几个年轻人高喊:“表演一下!”“来一次吧!”“大伙都等你哩!”许多人也跟着喊叫,不知他们要表演什么,我便悄悄地凑了上去。
只见张老汉坐在一块石头上,面前放着刚吃过的饭碗,眯着眼睛悠悠吸烟,他对大伙的呼唤不理。那呼声越来越高,叫声愈来愈大,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磕,插入怀中,单手托起饭碗,五指轻轻拨动,那只饭碗就顺时针旋转了起来。与此同时,他微微低头,张嘴伸出舌头,舌头贴着碗沿滑动,饭粒像扫地一样收拢到了嘴里。饭碗不停地旋转,他的舌头螺旋式向下,五指拨动也由慢加快,饭碗随着快慢的变化时而倾斜,时而归正,他的舌头越伸越长,舌尖扫过的饭碗圈圈向下,层次对接得严丝合缝,没留下任何空间,像精密计算过一样准确。快到碗底时,他的五指拨动更快,饭碗似乎飞了起来,有时好像扣在他的脸上,又没扣在脸上,他的舌尖在碗底扫动一下或两下,那碗高高抛了起来,时而扣下时而抛起,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张老汉舔完碗底留下的最后米粒,他把碗向空中高高抛起,双手接住侧转碗口向众人展示,吃罢的饭碗像清水洗过一样。众人拍手叫好。我心里赞叹,张老汉不是舔碗,他是在表演杂技。
看罢张老汉的表演,我想起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,中国的烹饪大师们,用肉食或海鲜,加上普通的面粉和蔬菜,做出了上千种独特、新鲜、爽口的美食,成为中华饮食文化的一绝!他们那套独特的工艺和烹调,也是一代代传下来,经过后人不断融合、改进、创新形成的。张老汉的舔碗技艺也是一绝。
(作者系陕西省作协会员)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在市级机关工作,经常下县驻队,多则一年,少者三四个月。吃的是派饭,每家一天,一户户挨着轮。自己给农户一斤粮票、三角钱,不足部分由上级补助。每到吃饭时,有主家的小孩来叫。进入家门,便脱鞋上炕,盘腿而坐。农村人讲礼仪,他们把工作组当客人,吃饭由长者或有身份的人陪同,其他人不能坐炕。炕桌早已摆好,擦抹得很干净,饭菜端上桌,长者礼让三先,他说:“请,吃,请吃饭。”吃完一碗,由儿媳或姑娘双手再端上一碗,这套礼仪一成不变。在农村工作期间,我发现他们特别爱惜粮食。夏收时,大人在前面割麦,娃娃排成横队,手提竹篮,在后面觅拾遗掉下的麦穗,力争颗粒归仓。他们吃馍时,双手捧着就在嘴边吃,馍的渣渣就不会掉到地上,偶尔掉下一半粒,也要从地上拾起塞入口内。
我在每家吃饭时看到,主妇把锅底铲得很干净,特别是打搅团,锅底留的饭底很厚,她们撒上少许盐巴,灶内添柴焙干,锅巴烤得焦黄,脆生生很好吃。他们吃完饭都用舌头舔碗,把碗内留下的饭粒都舔干净。我是从豫北农家走出来的学生,老家的大人教训孩子爱惜粮食,总是说:“把饭碗刮干净,如留下了饭根,会减你小命的寿!”但从不用舌头舔碗。入乡随俗,我吃毕饭也学舔碗,脸和鼻尖上沾了许多饭粒,花脸似的难看,惹得他们哈哈大笑,急忙递过毛巾或帮我擦拭。
我这个人有股犟劲,越是学不会的越要学。每吃毕饭,就请主家教我舔碗,他们笑着说,“我们舔的不到家,你向张老汉学吧,他是俺村的舔碗高手。”张老汉我认识,他六七十岁的年纪,留一把山羊胡子,手脚利索,是种田的把式。我曾在他家吃过两次饭,但没见过他舔碗。问他儿子,他儿子说,你们是城里人,我爸怕你们笑话。我说,这有什么可笑话?我还要向他学习哩!我的话是否转告给张老汉,我不知道。又在他家吃饭时说到舔碗,张老汉说,还不是个穷,老祖宗节约,爱惜颗粒粮食,吃罢饭用舌头把饭碗内的米粒舔个干净,就这样代代延续了下来,形成了一种习俗。我心里想,这是节约粮食的优良传统,是一种好习俗,也是一种饮食文化吧。
我见识张老汉舔碗是在一次“老碗会”上。农村人吃饭,大都端着饭碗聚在门口,一边吃一边扯闲,说说笑笑十分热闹,故称“老碗会”。当时,我从一家吃过饭走出门,就见“老碗会”上有人起哄,只听几个年轻人高喊:“表演一下!”“来一次吧!”“大伙都等你哩!”许多人也跟着喊叫,不知他们要表演什么,我便悄悄地凑了上去。
只见张老汉坐在一块石头上,面前放着刚吃过的饭碗,眯着眼睛悠悠吸烟,他对大伙的呼唤不理。那呼声越来越高,叫声愈来愈大,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磕,插入怀中,单手托起饭碗,五指轻轻拨动,那只饭碗就顺时针旋转了起来。与此同时,他微微低头,张嘴伸出舌头,舌头贴着碗沿滑动,饭粒像扫地一样收拢到了嘴里。饭碗不停地旋转,他的舌头螺旋式向下,五指拨动也由慢加快,饭碗随着快慢的变化时而倾斜,时而归正,他的舌头越伸越长,舌尖扫过的饭碗圈圈向下,层次对接得严丝合缝,没留下任何空间,像精密计算过一样准确。快到碗底时,他的五指拨动更快,饭碗似乎飞了起来,有时好像扣在他的脸上,又没扣在脸上,他的舌尖在碗底扫动一下或两下,那碗高高抛了起来,时而扣下时而抛起,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张老汉舔完碗底留下的最后米粒,他把碗向空中高高抛起,双手接住侧转碗口向众人展示,吃罢的饭碗像清水洗过一样。众人拍手叫好。我心里赞叹,张老汉不是舔碗,他是在表演杂技。
看罢张老汉的表演,我想起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,中国的烹饪大师们,用肉食或海鲜,加上普通的面粉和蔬菜,做出了上千种独特、新鲜、爽口的美食,成为中华饮食文化的一绝!他们那套独特的工艺和烹调,也是一代代传下来,经过后人不断融合、改进、创新形成的。张老汉的舔碗技艺也是一绝。
(作者系陕西省作协会员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