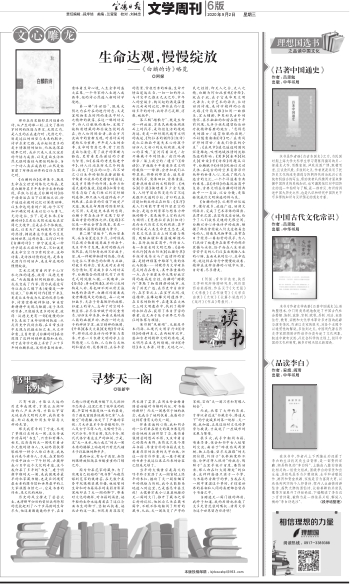本期发布:
生命达观,慢慢绽放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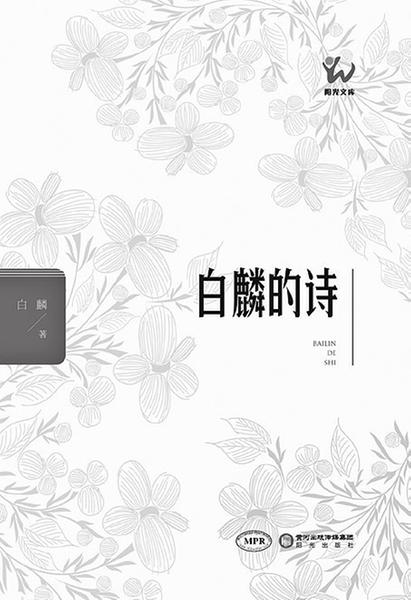
◎阿探
那些在历史暗影里闪烁着的诗,从产生的那一刻,注定了要洞穿时间的阻隔与界定。光阴之内,是人生的正在进行时;光阴之外,则是过往的回望与未来的期许。诗学求索之路,或许起初更多的是才情激情的炫灿。而抵达深层境界之时,或许只是人生沉淀后的开悟与成熟,以及直面生活坦然无惧的感性与理性的融合。当一个诗人真正成熟时,必然是他重建了对惨淡世界的信任与宽容之时。
《白麟的诗》这部集子,既是生命在尘世里的炼化之结晶,更是白麟对其多年来诗学求索的检视、萃取与创造。《白麟的诗》给予读者活在当下以理性之识,给予遥远永逝的记忆以深情回眸,以生命达观者的广阔,给予不可知不确定的未来以信心与勇气。无论过往、当下,还是未来,《白麟的诗》总是让光阴永远处在宏阔之大境中,总是去尽个体狭隘、逼仄,以更为广远的视野与空前的热情,拥抱着这个迷离乃至失性的世界。这部诗集,又何以叫作《白麟的诗》?毋宁说这是一种诗学追求之旅的命名,不如说更是生命空空乃万有的宣示。这部诗集,是诗性诗情的达观,是来自光阴内外的回声,是生命达观的慢慢绽放。
艺术之境有着洞穿千山万水之阻的通感。彼得·汉德克曾说,“而我随着时间的推移,彻彻底底变成了作家,因为我通过写作让我自己慢下来(缓慢是一种绽放)。”白麟的诗作《慢下来》,更是让生命成为从容的风景与畅享。诗意需要凝神体悟,审美需要静静中发现与触摸,过于急促的节奏,只能错失更多的风景。彼得·汉德克更有一部《缓慢的归乡》,表述了生命回转的轨迹:从反历史中找到出路,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与把握永恒之美。从文学命意、主旨考量,《白麟的诗》真实深隐了这样的精神进路和走向。对于在诗学之路上求索了三十多年的白麟来说,这部诗集的面世,意味着生命心境、人生金季的盛大启幕。一个作家的人生进入成熟季,他的诗必然进入新的诗学境地。
第一辑“浮世绘”,既是光阴之内在外在的进行时态,又是客观物象在时间的漫流中对人之精神的激荡。在这一辑的诗篇中,诗人以敏锐的感知,发现了被物质埋藏的那些被忽视的存在。诗人如同炼金者,源自岁月流淌中的重新发现,对其诗篇的建构尤为重要。中年是人生的金季、生命的智慧之季,有了坦然直面与接受,有了放手的果断与豁达,更有着更高谋划的力量与智慧。如《善谋的老虎钻进中年》,诗人以站在时光之外的高位,放走了过往的心念,而不甘之心以生命的韧劲在潜滋暗长中做着不放弃的更精密的谋划。这是岁月赐予的开阔,生命力和通天道的盛放。《迷路》如寓言般形象勾绘了我们难以判定对错的选择,那只误入歧途终成干尸的麻雀,在欲望的引领下被焚尸灭迹,既是生命周围的险象环生之写照,又是迷失本真的悲剧。白麟于常态生活中发现了哲学层面考量的理性之识,《迷路》不仅是一种社会常态现象,更是一种清醒而温情的提醒与警示。
第二辑“望故乡”,犹如望春风,妥当安置过往岁月。小时候我们在竭力做着逃离故乡的奋斗,及至中年才发现,来时的路或许依然在,我们却再也回不去故乡。望,是一种凝神融情的伤感,亦是与过往人事物态的和解与共融。对故乡的牵念,首先是对至亲的思念情切。有关故乡亲人的诗篇中,白麟饱含的深情化作了归有光式的纯澈入微,一线魂牵,如《登高》;再如《倒退》,淤积心底的物是人非,再也回不到从前至诚相感的奔涌中,白麟亦传递着我爱世缘随风定的豁达。每一次回归故乡,无异于青春做伴的放歌,归途上的诗人,忘却了时空的斗转星移,去尽俗世赋予的沉重背负,回归生命本真,和着天籁地籁人籁的幽微声动,把控一时之庄子的神游万里、放空精神的驰骋。《开犁》《春天大集》《麦穗》等诗篇中,那些流动在诗行的事体与意象,开启一片农耕文明的净土自然情境:人与物,人与物与天地的和谐正动,花香满径,五谷丰登的愿景,雪夜思亲的难挨,生命开悟后遥远反刍,一切一切的对立与冲突早已推至九天之外。中年人的望故乡,钩沉起的满是温情而沉甸甸的记忆,那些在内心盘结多年的对峙,此时早已瓦解、消散、被抚平。
第三辑“踏歌行”,既是生命的一种放逐,亦是民族根性溯源而上的找寻,是诗性复活的境地再造,更是一种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叛逆。《阿拉善的额际》(组诗)是红尘物欲中迷失本心的孩子回归人文初心的反向溯源,是诗心的召唤。“星河闪着泪光/打开掩藏千年的经卷/请你吟诵母亲/架上夜空的/遗言”(《母语》),穿越数千年漫漫历史文明的载体——母语,会告知我们从哪里来,将要到哪里去,迷失者需要找寻、需要回归、需要重温,需要找回意识的文明胸怀;《峡谷》《沙漠》掩埋着多少金戈铁马,人对宇宙自然变迁而言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沙粒,古旧的正在消退如新生的正在积聚;《星河》是人们难能可贵的仰望星空的机会,是远方的景深与想象力神驰的赐予,更是城市上空的天问与顿明;《曼德拉岩画》(组诗)是向古代历史文化的溯源,其中的诗篇是人类生命史生态史,是历史文化在岩石上的定格与凝固,残酷血腥和着温暖辉煌而生,在对抗性震荡中,开辟出人类一条漫长的文明之路;《嘉峪关纪行》《西出阳关》《北疆行草》等组诗是苍凉与广远情怀的重温,是精神颓萎中雄浑气质的体认与提振……诗歌作为文学母本范式的存在意义,其中很重要的一点,在于营建生命无限舒放空间的超高延宕性。白麟的“踏歌行”罢黜了物质拥挤的城市,走向了洪荒广远,在历史中自由穿行,在穹苍之上,在星宇之间,俊逸精神,在缘起缘灭的遗落中,在日晷的轮转中,在遗落在大地之上的文明遗存中,找到了精神的永恒存在,获得了来自宇宙的雅量,这无异于处于世界之外高位的体察与顿悟。
第四辑“风雅颂”,无疑是寻本问源,从现代文明穿行到《诗经》的精神本义,在两相对比中,感知古老的精神文明的质地,是文明内在生息的续魂。回到《诗经》本义本源,诗者,天地之心,民之性情,即天人之合、天人之精。白麟为何如此重视《诗经》,就在于此,在于它是华夏文明之源头,文学艺术的源头。让诗回到诗境,是诗学精神的必由之路。《竹简风雅》如同一曲雅乐,宏大铺排,华夏初民古朴的情怀,其乐融融的和谐在数千年前闪现,无异于祖先遗留给后世疗救精神萎靡的绝方:“患得患失的路口/迷茫难眠的夜晚/不妨随意翻翻《诗》吧/在清风旷野的前世/看我们伪装的今生”;《在风中》追忆遥远的国风烂漫雄起,叹喟地域性情的流脉悠远的影响;《葛覃》《卷耳》《桃夭》《甘棠》等《诗经》同题篇目中,白麟赋予《诗经》风物以灵动灵性,在远古的时空里复原淳朴纯粹的世情人心,完成了现代与远古的交汇。一个个洋溢着古典的意象,在《诗经》的春风浩荡中复苏,古典文明在白麟的诗情奔放中一一复活,以古为镜,更能检视我们文明演进的得与失。
《白麟的诗》,从都市世俗起步,慢行故乡,放逐广远,回溯文明源头,完成了艺术淬炼的圆熟,在渭水之滨,在宝鸡这座古城,给予了人们放养灵魂的无限空间。白麟以诗心诗性诗学的成熟,触摸了那些曾经被人们太过轻易忽略的人、情感及风物事体,在常态日子经历一番彻骨的找寻,为人们找回了被遗弃在庸常中的那些震撼与永恒,给予尚在人生苦旅苦苦寻觅的人们以直面残酷人生的心胸,直面未来的信心。生命达观,就这样在诗行中慢慢绽放着,精神在这种恬静的心境中从容、自舒着,尽享静美。
(阿探:青年评论家,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,现任职西安某高校。作品见于《文艺报》《文学报》《名作欣赏》《文学自由谈》《大家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《延河》《作品》等报刊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