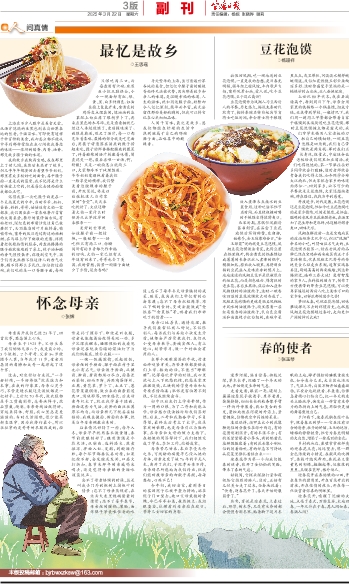本期发布:
怀念母亲
母亲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,回首往事,思念涌上心头。
母亲生于1925年,父母生养了我们姊妹兄弟6个,我是最小的,3个姐姐、2个哥哥。父亲56岁便撒手人寰,当年我才11岁,母亲用孱弱的肩膀和大哥一起撑起了这个家。
过去,对农村妇女来说,“一手好针线,一手好茶饭”就是能力和本事。在我的印象里,母亲心灵手巧,不管是缝衣服还是做饭都是一把好手。上世纪70年代,做衣服都是手工剪裁制作,先要画样子,然后剪裁、缝制。母亲针线活做得好,穿起来得体、舒服,我心里总是美滋滋的。当时生活困难,很少能买新衣服穿。因为我排行最小,所以往往穿的是哥哥的衣服改成的,经常是补丁摞补丁。即使是旧衣服,母亲也能想着法做得美观一些。多少次深夜醒来,睡眼惺忪的我看见母亲还在炕头昏暗的煤油灯下为我们纳鞋底、缝补衣服……
一粥一饭藏深情。说起做饭,母亲做的手擀面、臊子面在村子里也小有名气。母亲做手擀面,从搋面、擀面、剺面都用心尽力,面条长而柔韧、细而不断。再用鸡蛋饼丝、豆腐、黄花菜、萝卜丁、土豆丁、葱花等菜蔬调汤,做出来的面条筋道爽口,汤味醇厚,回味悠长。后来母亲年纪大了,就让我学着干揉面、擀面这些力气活。我擀的面往往薄厚不均匀,而母亲擀几下就妥妥帖帖的。我现在搋面、擀面的本事,就是当年母亲调教出来的。
后来情况好转了一些,每年入冬,母亲早早就用黍米做黄酒,春节前就酿制好了。酿制黄酒是个技术活,从制曲、选料浸米、蒸煮摊凉、拌曲入缸、发酵,到酘酒存贮,每个环节都要认真对待,如果把控不好,会发酸或发苦,口感大打折扣。春节来拜年的亲戚喝来喝去,还是觉得母亲酿的黄酒味道最纯正。
忘不了母亲烙馍的时候,总是叫我去门外的椒树上摘椒叶的情景;忘不了母亲蒸馍前,在灶头火灰里烧碱蛋蛋的情景;忘不了每年春节,母亲做的暖锅、灌肠、油炸馃子等美味佳肴的味道;忘不了每年冬天母亲腌制的咸菜、酸菜,成为我们上学仅有的必备菜蔬;忘不了母亲把极简单、难以下咽的食材,变戏法般做成“金银卷”“金裹银”等,哄着我们乖乖吃了的情景……
母亲心地善良、通情达理,教导我们要常记别人好处,不记恨别人。每当我们与其他小孩发生矛盾,她都会严厉管教我们。我们从小受母亲教导,要诚实做人,有上进心,刻苦学习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,母亲始终咬紧牙关,再苦再难都要供我们上学。按她的话,不能当“睁眼瞎”。记得每次开学的时候,我心里就七上八下犯愁犯怵,犯愁是家里拮据没钱,几块钱的学费母亲和大哥要东借西凑;犯怵是害怕筹不到钱,不让我继续念书。
初中以后我们上学要带馍,作为一周的口粮。为了二哥和我能上学,母亲想方设法按时给我们蒸好馍。后来,二哥和我勤奋学习,不负厚望,最终先后考上了大学,这是家庭的荣耀,也是母亲引以为傲的事。在母亲和大哥的倾力支持下,在姐姐的周济帮衬下,我们相继完成了学业,参加工作,结婚成家。
母亲苦尽甘来,本应享受天伦之乐,可残酷的病魔早已侵入她的身体,母亲走完了她76年的平凡人生,离开了我们。子欲孝而亲不待,母亲竭尽所能地为我们付出,但我们能回报母亲的却微乎其微,每每想起,心痛不已!
今年初,我回老家,看到昔日的窑洞院子已被平整为耕地,站在院子门口望去,坡口父母栽植的青槐,今已亭亭如盖,巍然挺立。我泪眼婆娑,依稀看到母亲站在坡口,等待儿女回家的身影。
母亲生于1925年,父母生养了我们姊妹兄弟6个,我是最小的,3个姐姐、2个哥哥。父亲56岁便撒手人寰,当年我才11岁,母亲用孱弱的肩膀和大哥一起撑起了这个家。
过去,对农村妇女来说,“一手好针线,一手好茶饭”就是能力和本事。在我的印象里,母亲心灵手巧,不管是缝衣服还是做饭都是一把好手。上世纪70年代,做衣服都是手工剪裁制作,先要画样子,然后剪裁、缝制。母亲针线活做得好,穿起来得体、舒服,我心里总是美滋滋的。当时生活困难,很少能买新衣服穿。因为我排行最小,所以往往穿的是哥哥的衣服改成的,经常是补丁摞补丁。即使是旧衣服,母亲也能想着法做得美观一些。多少次深夜醒来,睡眼惺忪的我看见母亲还在炕头昏暗的煤油灯下为我们纳鞋底、缝补衣服……
一粥一饭藏深情。说起做饭,母亲做的手擀面、臊子面在村子里也小有名气。母亲做手擀面,从搋面、擀面、剺面都用心尽力,面条长而柔韧、细而不断。再用鸡蛋饼丝、豆腐、黄花菜、萝卜丁、土豆丁、葱花等菜蔬调汤,做出来的面条筋道爽口,汤味醇厚,回味悠长。后来母亲年纪大了,就让我学着干揉面、擀面这些力气活。我擀的面往往薄厚不均匀,而母亲擀几下就妥妥帖帖的。我现在搋面、擀面的本事,就是当年母亲调教出来的。
后来情况好转了一些,每年入冬,母亲早早就用黍米做黄酒,春节前就酿制好了。酿制黄酒是个技术活,从制曲、选料浸米、蒸煮摊凉、拌曲入缸、发酵,到酘酒存贮,每个环节都要认真对待,如果把控不好,会发酸或发苦,口感大打折扣。春节来拜年的亲戚喝来喝去,还是觉得母亲酿的黄酒味道最纯正。
忘不了母亲烙馍的时候,总是叫我去门外的椒树上摘椒叶的情景;忘不了母亲蒸馍前,在灶头火灰里烧碱蛋蛋的情景;忘不了每年春节,母亲做的暖锅、灌肠、油炸馃子等美味佳肴的味道;忘不了每年冬天母亲腌制的咸菜、酸菜,成为我们上学仅有的必备菜蔬;忘不了母亲把极简单、难以下咽的食材,变戏法般做成“金银卷”“金裹银”等,哄着我们乖乖吃了的情景……
母亲心地善良、通情达理,教导我们要常记别人好处,不记恨别人。每当我们与其他小孩发生矛盾,她都会严厉管教我们。我们从小受母亲教导,要诚实做人,有上进心,刻苦学习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,母亲始终咬紧牙关,再苦再难都要供我们上学。按她的话,不能当“睁眼瞎”。记得每次开学的时候,我心里就七上八下犯愁犯怵,犯愁是家里拮据没钱,几块钱的学费母亲和大哥要东借西凑;犯怵是害怕筹不到钱,不让我继续念书。
初中以后我们上学要带馍,作为一周的口粮。为了二哥和我能上学,母亲想方设法按时给我们蒸好馍。后来,二哥和我勤奋学习,不负厚望,最终先后考上了大学,这是家庭的荣耀,也是母亲引以为傲的事。在母亲和大哥的倾力支持下,在姐姐的周济帮衬下,我们相继完成了学业,参加工作,结婚成家。
母亲苦尽甘来,本应享受天伦之乐,可残酷的病魔早已侵入她的身体,母亲走完了她76年的平凡人生,离开了我们。子欲孝而亲不待,母亲竭尽所能地为我们付出,但我们能回报母亲的却微乎其微,每每想起,心痛不已!
今年初,我回老家,看到昔日的窑洞院子已被平整为耕地,站在院子门口望去,坡口父母栽植的青槐,今已亭亭如盖,巍然挺立。我泪眼婆娑,依稀看到母亲站在坡口,等待儿女回家的身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