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期发布:
边风乡愁三十年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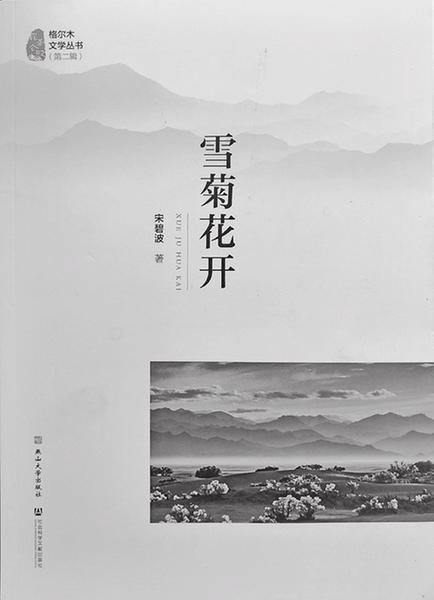
◎商子秦
又见到了宋碧波。三十多年的时光,让当年的西府帅哥,一下子变成了饱经风霜的中年汉子,真是感慨万千。碧波还在写诗,而且已是有所成就的西部诗人,我为之欣喜。尽管我们都不再年轻,但初心不改,诗情依旧。
读到他的诗集《雪菊花开》,收录其中的这些诗,一半写青藏高原,一半写故乡西府;一半是边城的风霜雪月,一半是故园的乡愁乡情,所以,当我想写下一点对这些诗作的读后感时,脑海中立刻就出现了“边风乡愁三十年”。
先说“边风”。这个词很有历史,唐代诗人武元衡有“边风送征雁”,苏颋有“边风思鞞鼓”,宋代诗人梅尧臣有“边风惨惨听胡笳”。碧波所在的格尔木,位于柴达木腹地,是进出西藏的门户,用这个词来表示没什么不妥。在这些“边风”类的诗作中,碧波写了青海最具标志性的青海湖、昆仑山口、可可西里、西部雅丹、达坂山、郭勒木德草原等壮美风光,也写了胡杨、红柳、雪菊花、白莲花和鹰、骆驼、藏羚羊等高原生命,读着碧波的诗作犹如旅行,眼前变幻着高原风光,心灵感受高原魂魄,美美地过了一把瘾。
碧波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,他的诗歌语言自然与时代同步,是一种开放和灵动、富有张力的诗的语言。读这些诗的时候,我常为之眼前一亮:像“峥嵘和狞厉,崇高和悲壮,是江湖上的过命兄弟”,“格尔木偏西的荒原,阳光给斑驳的意念打上青铜,时间在这里停歇发凉的脚印”等等,有着一种雄浑魅力。
而较之于语言,这些诗让我更为看好的是诗中的境界和情怀。在青藏高原生活三十多年之后,碧波已经和这片土地达到了一种心灵的默契,物我合一,诗中一个个鲜活的意象,表达了诗人的情怀。
《天边的红柳》中,“九死一生的一抹芳魂,坐拥一派玄黄,从不与远近的事物争辩”……
“曾经有几只比较抒情的藏羚羊,歪着脑袋将我仔细打量……在这可爱的高原精灵眼里,我,会是个什么意思,或者,谁的模样?”鉴于篇幅,不再更多地引用原作了,相信未来的读者在阅读时,自己会有更多的发现和感受。
碧波的“边风”类诗作中,有着老一辈青海诗人昌耀等人的苍凉冷峻的诗风,更有着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受,这些诗是写给高原的情歌,是对生命的礼赞和美的吟咏。可以说,因为有了这些诗,碧波在青海生活的这三十多年,那真是没有白过。
下来该说一说“乡愁”了。在这一部诗集中,这类诗作所占的比重更大一些。我理解,这些诗更多地表现出诗人生命另一种内涵,这就是游子情怀。碧波在格尔木工作三十多年,漂泊在异乡,是一位名副其实的“游子”。可以说,他就是用三十多年对故乡的思念,熬成了一首首有着浓郁乡愁的诗歌。
在这些诗作中,故乡有着悠久厚重的历史,是秦穆公雄霸一方的雍州,是北魏古城墙的遗迹,是苏东坡撰写《喜雨亭记》的小巷;故乡又是家园,是一架豇豆、一片红莲、一声乡音,甚至是一个正在“杀西瓜”的瓜摊;故乡还是亲情和友情,是外婆的名字,是同窗好友的相聚,甚至是童年那个“官打捉贼”的游戏;故乡更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久远记忆,这正像碧波的诗句:“原来所谓的远方,就是淹留岁月的原乡,是你年少时曾经厌离的地方,也是如今,只能在梦里亲近的故乡。”
在这些诗中,碧波写得最多的是“月”和“雪”。大概这两个意象,最容易引起思乡之情。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,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古来如此。在青海的无数个月明之夜,抬头看见月亮,碧波一定会想到西府古塬上家乡的月亮。雪也是一样,“青海长云暗雪山”,在青海多雪的日子里,诗人也一定会常常想起“散关三尺雪”,想起凤翔古城大雪纷飞的日子。有了三十多年酝酿,只要有一个契机点燃灵感,表达自然不同凡响。
读这些诗,常引起我的共鸣。从1968年赴宝鸡上山下乡到上世纪90年代末调离,我在宝鸡生活了三十年,度过青春岁月,留下无数难以忘怀的记忆。离别宝鸡二十年后的今天,正是这些氤氲着浓郁乡愁的诗行,让我真切地走回那熟悉的“第二故乡”,而数度掩面思远,心中久久难以平静。
所以,我感到碧波不但是一位优秀的新世纪“边塞”诗人,更是一位现今西部的“乡愁”诗人。这部《雪菊花开》的诗集是一部饱和度很高的“纯诗”,是一部和生命与灵魂交流的记录。我为碧波写出这样的诗作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在格尔木的三十多年,碧波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,居然还能够保持着这一份纯净的诗心和诗情,是难能可贵的。时光荏苒,如今的碧波已经过了“知天命”之年,进入了人生和艺术都已积淀深厚的成熟期,我希望也相信碧波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诗歌。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省诗词学会副会长、省赋学学会会长、西安市作协副主席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