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期发布:
初雪为欢谣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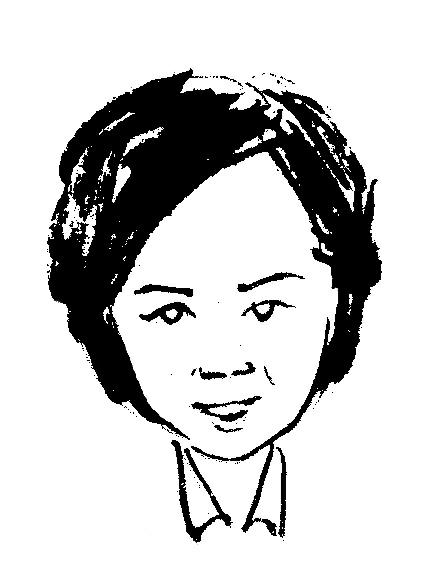 弓艳:军旅作家,陕西宝鸡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长篇小说《非常禁区》,散文集《心路》、报告文学集《国家救援——一切为了人民》等多次在军内外获奖。
弓艳:军旅作家,陕西宝鸡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长篇小说《非常禁区》,散文集《心路》、报告文学集《国家救援——一切为了人民》等多次在军内外获奖。 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。一夜间,千门万户雪花浮,被初雪覆盖的亭台楼阁,点点无声落瓦沟,美不胜收。
昨夜,梦见了父亲。不知道是否跟这场初雪有关。他已故去快九年了,最深的遗憾就是没能在父亲离世前见他最后一面,这不单单是我的遗憾,在我们军人身上尤其常见。
那年正月里,我值完班回家陪伴病重的父亲,突然单位有任务急催我回去,我接电话时父亲就在身边,是他把我“赶”走的。“回去吧,部队的事耽误不得”,这是有近三十年军龄的老兵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返京路上,雪下得很大,落在脸上,化雪为水,寒凉无比。那天的我似乎已有预感,此去可能永远见不到父亲了。
作为家里的长女,也是从父亲下葬那天开始,真正长大的。人到中年,经历过命运多舛、高地低谷的跌宕起伏,竟没有了从前父亲在世时那般对家的依恋。常羊山墓地的积雪未化,一路崎岖,我磕磕绊绊走得十分辛苦。抱着父亲的遗像,我默默流泪,在心里对自己说,从今天起,有多少困难你都得自己去扛,让母亲放心,让弟弟踏实,让这个家和从前一样仍有很多欢乐和希望。
内心要变得坚强并不容易。直到去年春节,我才和爱人在父亲去世后第一次回家过年。我们父女情深,不选择春节回家就是怕心里那种撕裂的疼过不去。吃过年夜饭,我们给父亲上过香,这个心结总算过去了。父亲在世时,我们常常聊起很多部队的趣事,研究生毕业前,我选了跟“三战”有关的论文课题,也是因为他珍藏了一套抗美援朝时期政治工作的宣传画册,我看完之后突发奇想,从那里破的题。虽然工作后,和家人聚少离多,但遇到事情常常会选择和父亲诉说,我们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,就像这次回家过年,我相信父亲定会知道,我们回来看他了。
今晨,泪未干,天没亮,人已醒。
打开手机,看到朋友圈里发的美图。故宫的角楼、颐和园的佛香阁、百望山下的营院……到处都被素雪覆盖,令人心驰神往。此刻的心情,是极想和这场雪亲近,不知是对一场茫茫大雪的渴望,还是内心深处对童年记忆的重温,或是对伤感过往的悲恸和怀念。
今年的雪下得不大,来得也很安静。一进单位的营门,看到红色条幅迎风飞舞,突然心生感动,这吉庆的红和圣洁的白,就是军队医院的底色和情怀。警卫执勤的战士们看来刚刚点完名,班长一声“解散”,他们一改往日的沉闷,像孩童般用手攥起了雪团子,互相追着瞄着战友们的后背和脖子,散发连发地打了起来。还有的被追上来灌了一脖子雪,脸上却无半点恼怒之色。这是劳动前的序曲,他们厚厚的迷彩大衣为这幅晴雪的画面又增添了一抹棕绿色。有的战士已经拿了扫把出来,在大马路上开始扫雪。他们的动作十分轻柔,和我小时候在部队大院里看到的可不一样。我印象里,小时候的冬季是一场雪接着一场雪地下,扫雪是北方冬天部队里最常见的体力活儿。我想,大概还是因为眼前这场雪来得有些珍贵,落得轻薄,来得让人舍不得拂掉它的痕迹吧。直到扫雪的队伍渐渐壮大起来,马路上才很快被清理了出来,成了一条细长蜿蜒干净的人行道。
此时,军号已响,扛着扫把的战士们鼻尖都渗出了细细密密的小汗珠,那些青春的脸庞红彤彤的,在班长的指挥下,列队走回连队。一位老人抱着小孙子,目不转睛地看着战士们稍息、立正、齐步走,全然不顾小孙子挣扎着想要下地去踩踩雪。老人那若有所思、望着队尾久久收不回来的眼神,让我猜想,他可能是位老兵吧。
雪后的百望山,在我眼里就是最美最熟悉的景观。
行走在通往山顶的路上,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是自然界最动听的声音,它带着记忆中一些特定的符号,被这场雪唤醒了。对,我又想起了小时候的营院——
晋东南山脉绵延千里,这个给了我最初梦想的地方,坐标也在太行山上,和百望山之间,它们会有某种联系吗?
山路陡滑,但我还是很快走到了山顶。眺望远处工作了快三十年的营院,我再次想起了小时候山坳坳里的雪天,那些挥舞着铁锹扫把的解放军叔叔,想必大多已到暮年。还有陪伴我玩耍的小伙伴和珍贵无比的童年,他们呢,后来都去哪了?匆匆忙忙,几十年的时间,弹指一挥。很多人疲于奔命,疏于联系,渐行渐远;有的只是在朋友圈偶尔闪过,然后又悄无声息,除了复制粘贴的节日问候外,没有更多的情感表达;还有的和我一样,心里惦记却不知整天在忙些什么,几年也见不上一面,等蓦然回首发现老友之珍贵时,已鬓发染霜。
踩雪下山的路有些湿滑,发现小心翼翼不如按自己的频率大步向前。哼着小曲儿,把昨日与友人热烈讨论的一些沉重的话题,一点点放下。
人生的乐趣,就是看雪赏雪时,能联想到当下的幸福来之不易,生活中,不必为了讨好谁而丢失自己,还有那些曾经以为的黑暗隧道,不过是我们人生必经的路径而已。接受成长,接受不尽如人意,接受不欢而散,接受得未曾有,初雪为欢谣,如此便好……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