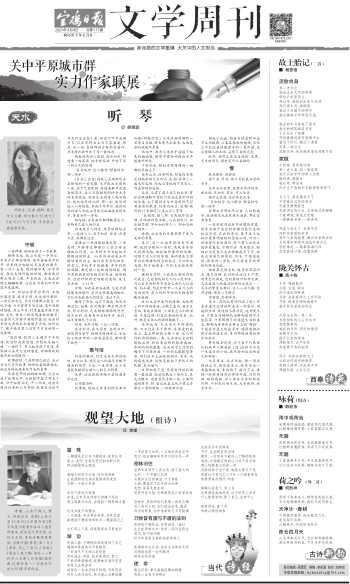本期发布:
听琴

胡晓宜:记者,编辑,做过电台主播。有文散见于《美文》《延河》《飞天》等,多次获甘肃省新闻奖。
守候
一曲弹罢,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
群峰深处,依山而建一个村庄,家家户户都会唱曲。每年春暖花开时节,村里便会响起悦耳清亮的歌声。有一对小夫妻,刚结婚不久,非常恩爱,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,都要面对群山唱会儿歌。声音既出,云朵也会随之翩翩起舞。这是在为他们炽烈的爱而欢喜呢。
一日,新妇如常外出劳作,不慎坠落悬崖,香消玉殒。丈夫闻听噩耗,一时悲恸不已,多日对着群山枯坐。不吃不喝,亦不曾有半句言语。某个寂静的傍晚,月上半弯,村里袅袅升起了炊烟。突然,传来一阵深情凄婉的歌声,让整村人听着听着黯然落泪,就连村里的大黄狗也和着歌声齐吠。细听之下,歌声原是男人沉默多日后的第一次哀鸣。
“想你哩,想得三天喝不下半碗汤,我想你是真想哩,你想我是骗人哩。”一曲终了,男人纵身跃下悬崖,身影融入漆黑无边的暮色,冷彻寒夜的歌声却如影随形……
故事很短,几分钟便已讲完。我以为它只是个故事,她却认真地看着我,说这是她从母亲处听来的真事。
年届花甲的她轻眯双眼,完全沉浸于故事之中,又轻轻哼起了那支小曲,目中似有泪光。平心而说,近些年因为记者的工作身份,我曾在采访中多次听过这类小曲,却由于听不大懂方言,实在觉得太土而不甚喜爱。但是,这一回,在她那间古致的琴房内,单单将此曲听出了另一番味道。
初春的风吹入窗棂,夜凉如水,仍透着一丝寒意。她手抚琴弦,开始了另一种方式的吟唱。
“月出皎兮。佼人僚兮。舒窈纠兮。劳心悄兮。”
《月出》,出自《诗经》,是她新近正在弹唱的一首琴歌。琴声较之先前的小曲,添了几丝优雅,伴随着歌声更显哀婉苍凉。让人不禁联想到诗中女子的美丽面容,深深感受到诗人越思越忧、越忧越思的沉郁。那一刻,恍然间进入一种情境,穿越千年岁月,彼时忧伤的诗人与站立悬崖边痴痴张望的汉子,重叠为同一身影。
她与他,正在满目期待眺望远方,等待自己爱人的归来。
同来望月人何在,风景依稀似去年。心爱的人儿,你可知道,你在,或者不在,我都在这里。
曾看过一部韩国纪录电影:《亲爱的,不要跨过那条江》。在江原道横城山村里,98岁的老爷爷赵炳万像强壮的樵夫,89岁的奶奶姜溪烈像娇羞的公主,他们在雪里吃初雪,堆雪人,手拉手才能睡着,身穿的传统韩服,都是精心搭配的情侣装。倘不是画面里的电饭煲和电话,很难相信,这世外桃源里的绝世爱情,发生在当世。2014年。
守候,如此美好与决绝。它是对爱情最美的歌颂,是对生命最高的咏叹,古往今来最动人的情感,莫过于此。
辗转了命运,注定了邂逅,却天涯两茫茫。如果,清风有情,那么明月可鉴,斩不断的,是我缠缠绵绵的思念,绕不出的,是匆匆而过的年华。我们,从不曾相忘于江湖。
转身,安然守候。心与心对望。
在音乐间,在电影里,在现实中,爱情因为坚守,被赋予特殊意义。它让红尘俗世中的一份普通情感,瞬时有了禅意……
雅与俗
对爱的歌颂,对生活与生命的咏叹,自古以来,便是文人们最愿意赋予精力的创作。于我,一直觉得,此亦是最能在瞬间打动人心的艺术特质。
或许,这就是情感赋予其的最奇妙之处。
以琴歌为例。
记事起,便从父亲录制的琴曲中知晓《阳春白雪》,它是战国时期的一首著名琴歌,弹奏着冬去春来、大地复苏的欣欣然景象。
记忆中,每当父亲的手指按下红色的播放键,磁带中便会响起如水声般动听的琴。
少时的我,瞬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似乎静止了……
读书之后,逐渐明白,阳春白雪原是指高雅的艺术形式,出自《楚辞》,一般来形容雅。而大众常说的下里巴人,则通常被形容俗。
后来,又有了属于自己的古琴,有机会现场聆听曾经只能在光盘中听到的琴歌,也了解到古琴中原有许多抒写爱情的歌曲。仅李白而言,就有《秋风词》《长相思》《关山月》,等等。
“长相思,摧心肝。日色欲尽花含烟,月明欲诉愁不眠;入我相思门,知我相思苦。早知如此绊人心,何如当初莫相识……”
诗歌,让古老的乐器拥有了更为美好的意象。
某日,与一位通音律的老师闲聊。说到琴歌与小曲时,谈及音乐形式的雅与俗。他说他印象中的琴歌,仅限于文人们的吟唱,属闲愁或悲愤等自我情绪和情感的表达,可以称之为雅,但于他看来,实际上也就是矜持一些。
据相关资料,小曲是山歌的内敛化表达,已经由民间艺人们二度加工,可以在室内和年节庙会上由艺人们演唱。而山歌,则是旷野中一人或几人的自由创作,是人性和个性的无拘束舒展与张扬。
我们生活中爱听的情歌,大抵有三种不同的情状。山歌式表白,粗犷且直白,豪迈且畅快;小曲类艺人们的演唱,多属逗趣、引笑或委婉的意会;此外,便是文化人的诗词歌赋了。
老师认为,艺术形式中所谓的雅,只不过是多了修饰。在情爱的表达上,真正将好的山歌小曲、文人创作的诗词相较一番,无法评述受众的雅俗之分。好比李清照的暗香盈袖、秦观的朝朝暮暮;信天游中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、一对对毛眼眼望哥哥、咱们拉不上话就招招手,等等。从传唱度来讲,反倒是貌似下里巴人的民歌,更为动人。
我仔细想了想,觉得老师说的很有一番道理。仅就琴歌与小曲而言,在大众眼中,前者显然古雅一些,小曲则通俗得多。但,若让我真正从实质上去界定二者的雅俗,一时真难定论。
朋友Y也说,倘若为情爱附加过多文化腔调,以至其高尚和高雅,实际上早已远离情歌原本的心灵冲动,失去情歌人的本性,没有了真情实感。
既然,相思之意无关雅俗,足见,艺术的形式,随时是可以共融的。
慢
时光静些,再静些。
慢下来。听琴。读几页线装书里的句子。
琴声与书页里,呈有古早的诗意。秋之夜,凉如水。有光,可入琴音。
若你正忧伤,这忧伤会变美。
“月出皎兮。佼人僚兮。舒窈纠兮。劳心悄兮。”
在那么早那么早以前,人们悠哉兮,就连相思也是优雅而漫长,那么富有诗意。
一直钟爱月出时节的朦胧意象,经年沉溺于苍茫时分踏月色行走的恬淡感觉。在我的身边,很多友人大抵热爱黎明破晓时登临山顶,只为一观喷薄而出的朝阳,鲜少有人如我这般热爱暮色,守候月出。思来想去,起初以为是自己生性懒散起不了早,抑或是深藏悲剧情结。后来,才慢慢发现,原来内心深处,终究喜爱月的那份沉静与从容。
细数落花因坐久,缓寻芳草得归迟。很多时候,我们的生活过于严肃,时常忘记微笑,忘记看树叶如何变黄,忘记看鸟儿的翅羽如何划过长空……太多的繁复与匆忙,让人心浮气躁。觉得浮躁,那是心不够定。
需要慢。需要休息。
米兰.昆德拉有部作品,《慢》。作者在虚实之间始终追求一种曼妙、闲适的生活。读过的人很清楚,这种慢生活,只有在对精神的消解和建构中才能获得。只有解构了对快速生活的追求,解构为荣誉而在舞台上的“舞蹈”,才能在对虚无的追寻中,懂得建构如何才能闲适生活,享用那份独有的快乐与真实。
有时候会觉得,对于当下行色匆忙的城市人群来说,《慢》或许并不是一本适宜的小说,徒然增加自我的否定和烦恼。
九月将末,天凉风起。择一周末晴好之日,独登慧音山,特意感受一番暮秋之美。夕阳西下,缓行下山,看到一轮晕黄的弯月徐徐升起。日月同辉,阴阳两极,如小曲与古琴的雅俗对照,亦如我们的生活,左手倒影,右手年华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