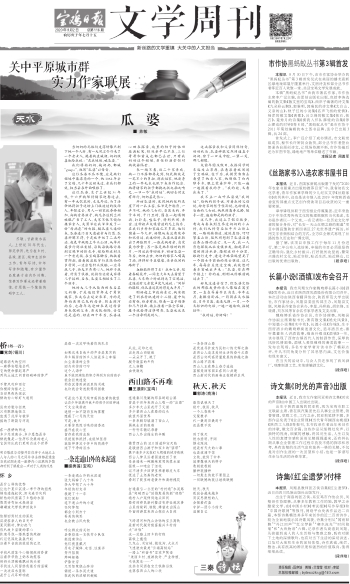本期发布:
瓜婆

苏敏:甘肃清水县人,上世纪70年代生,师范学历,先后在乡村、县城、景区、城市生活和工作。青年写诗,中年写诗和随笔,有少量作品发表于省内外刊物。信奉写作要永远带着感情,甘愿做一个笨拙的码字工人。
当奶奶的兄妹们走得好像只剩下她一个人时,有一天风尘仆仆来了一个老女人,抱着她直喊姐。奶奶欣喜地给我说:“是我妹妹,喊瓜婆。”
我们将姑奶奶、姨奶奶,都喊“guapo”,权写“瓜婆”以传音。
这位瓜婆不瓜不傻,应是她们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。她1962年去了宝鸡,几十年没回来过,亲戚们都说,权当丢在外面喂狼了。
这位瓜婆,生于上世纪30年代,十六岁被邻村杨家迎娶过去,有一年大饥荒时,丈夫外逃,为了活命她将孩子送给上门收娃娃的陕西人。年馑过去,男人一回家就拳棒相加,向她索要孩子,她无奈逃到兰州被服厂当了工人。夫家不依不饶向娘家索人,大舅爷让我爷爷发了一份“母病危”的电报,骗瓜婆火速回来,瓜婆进门后又遭谴责与打骂。瓜婆辩解不得,于是就开始了二次外逃。夜色中她爬上牛头山顶,从草川梁步行到社棠镇,沿陇海铁路讨要到宝鸡市的卧龙寺,嫁给附近村庄一个老光棍。在宝鸡落脚后,她挑着货郎担,摇着拨浪鼓穿行在陕西的乡村间,一边出售针头线脑,一边寻找儿子,功夫不负有心人,她终于找着,付清了钱粮,就捎信让前夫家将儿子接回。后来,瓜婆又相继生了三个孩子。
她的大儿子从陕西回来后其父新娶,于是他经常奔走于舅家姨家,长大后去延安参军,为的是奔向离别已久的母亲。转业到河南后,也每年远途回来见过母亲再来探视父亲,虽关陇相隔,音信还是通的。好在四十年后,瓜婆决心回来探亲,峡里的柿子树依旧挂满红果,但双亲早已不在,三位哥哥和前夫也都已去世,只有我奶奶这个姐姐,虽侄孙满堂但对她恍若隔世。
来一趟不易,近二十家亲戚,她一门不落都要走到,仅礼物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到我姑家,她连身上的一件毛衣也脱下来当作纪念。她将诸家的孩子都抱之抚之拍之啃之,一口一个“我的娃”。她回去时没有辞行,奶奶甚是伤心。
拜访瓜婆时,发现她的住所是崖下的一孔土窑,瓜爷是个驼背,一声不吭。她的儿女们,当医生的、开卡车的、干门卫的,围在一起喝稠酒、打扑克、嗑瓜子,特别热闹、亲密。这种粗声大嗓营造的无上快乐,在我们乡村和家庭已不多见。他们围着一个火炉,好像从来没有寒冷和忧伤过。我返回时,瓜婆从箱底取出了两张照片,一张是她母亲,自觉最为珍贵;另一张是她年轻时的照片,一同送我带回故乡。回访瓜婆一年后,奶奶去世,奶奶的娘家人喝高了酒,摔掉杯子直嚷嚷,老亲戚间的路断了。
血脉能断得了么?我和父亲,趁着春暖花开,一同坐火车又去看望了瓜婆。火车两小时就到达了宝鸡站,过隧道时父亲瓮声瓮气地说:“同样的路程,你瓜婆逃荒时得走大半月。”
刚好赶上市政府东迁,她家搬进了新农村统建的小二楼。屋中炕边有柜,柜旁有灶,堆着一篮子鸡蛋和几斤挂面。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,屋子收拾得洁净明亮。瓜婆永远是一个洁净明亮的人。
这次探亲我和父亲同样惊奇,奶奶死后,瓜婆神貌突然间逼真于奶奶。除了一口关中腔,一颦一笑,哪儿都像。
大前年国庆假日,我搭同学的车逛关山草原,浪着浪着就闯进了宝鸡城。住下后,我摸黑匆匆去看望了她老人家,她刚做了白内障手术,眼上蒙着纱布,只能一遍一遍摸着我的手:“我的娃,又看我来了。”
我不止一次听瓜婆说“我的娃”,给她的孩子说,对着我的父母说,给老家的侄子侄孙说,也给前夫后面的儿女说。她熬到高寿之龄,随手一捡,遍地都是她的孩子。
这几年,我迷上了假日徒步,有次与妻来到生养过奶奶的小山村,我们从村背后往牛头山顶上爬,一路荆棘锁道,坡陡崖险,吁吁攀至山顶,猛然间想到了瓜婆沿着这条山路的逃亡。又一次,我一人背包挥杖从社棠镇出发,翻越草川梁回到清水县,路程近四十公里,踉跄行走中,透过汗珠蒙眬望见了一个弱女子前面的愁云锁道。这几年,每每出差经过宝鸡,我就想对着车窗喊出声来:“瓜婆,你在哪个楼上?你的娃,刚刚从你眼前跑过去了。”
好久没通音信了,但瓜婆交给我的那张发黄的老人像贴在寓室里,一直在等着什么消息。今年正月,妻腰伤卧床,一同困在天水躲疫,日升日落,漫漫无期。一日,一个无标识的电话,一遍一遍地响,按键接听:
“我的娃,你好吗?”